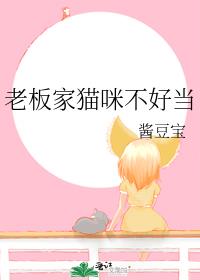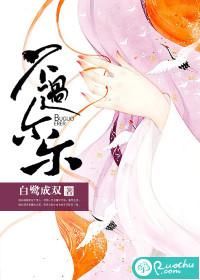京都百俠圖 - 第 24 章 江湖水音(1)
光緒年間。那個風雨飄搖的日子。
被稱為京津南大門的直隸滄州,歷代都是南北往來的要沖,又是多慷慨悲歌壯士的武術之鄉。由于滄州地濱渤海,荒涼貧瘠,史稱“遠惡郡州”,為犯人發配之地,也是失意拳師和被官府追緝的俠客隐身之地。再加上歷代戰亂,兵匪屢起,為了強身自衛,習武亦成滄州遺風,武林高手也層出不窮。
這天黃昏,一抹晚霞斜倚在任英屯的西側,河上的老柳歪歪的,梢頭挂着點光彩。河裏沒有多少水,幾個光腚的孩子和一個無賴正在戲水;河水發出一些微腥的潮味。河面上漂浮着玉米葉,卷起些細碎的小水泡。袁家院子很清雅,挂滿絲瓜、豆莢的籬笆上,綠油油的葉子沐浴在溫煦的陽光下;三間房的北屋,炊煙袅袅地從屋頂上飄起……
一個青年漢子正坐在石凳上狂飲,石桌上放着一碟腌黃瓜和幾個燒糊了的老玉米,旁邊有個大酒壇。那漢子紅堂堂的臉盤,鼓棱棱的肌肉,黑得透亮。兩只眼睛,熠熠有神。
這時,遠處傳來一陣豪邁的歌聲……
塵心撇下,
虛名不挂,
種園桑棗團茅廈。
笑喧嘩,
醉麻查,
悶來閑訪漁樵話。
高卧綠蔭清味雅。
栽,
三徑花。
看,
一段瓜。
歌聲豪邁,在原野上打着旋兒……
一忽兒,樹林裏轉出一個老僧,騎着一頭毛驢,慢悠悠而來。他頭戴玄色緞僧帽,身穿繭綢僧衣,手裏拿着數珠。老僧騎驢來到院裏,對青年漢子說:“走路累了,來口酒喝。”
青年漢子細看老僧:他形骨古怪,相貌驺瘦,卻是水樣的秀美、飄逸。
青年漢子見來者不凡,連忙起身,拱手說道:“老師父請坐。”
那老僧也不客氣,從驢背上一欠身,如葉落地,正坐在青年漢子的對面石凳上。
“老師父從哪裏來?”
“不要問我從哪裏來,也不要問我到哪裏去?拿酒來!”老僧的嘴蹭了蹭袖子。
青年漢子用空碗舀了滿碗,遞給老僧。
“拿兩個空壇子來!”
青年漢子不敢怠慢,搬來兩個空壇子。老僧脫去草鞋,赤腳放在空壇之中,然後雙手抱起大酒壇,咕嘟咕嘟地喝起來,喉間發出咕咚咕咚的聲音。轉眼之間,一壇酒告罄。
青年漢子看得呆了。
老僧将酒壇放下,毫無醉意;他從空壇裏拔出腳。青年漢子見他腳踵間酒液淋漓,足趾間酒氣氤氲;再看兩只空壇,已經酒滿欲盈。
“老師父,這是怎麽回事?”他問。
老僧朗朗笑道:“這算不了什麽,老納不過善運氣而已。這一壇酒,雖然喝進腹中,但是運氣下達,驅酒從足心湧出,別的就沒有什麽了。”
青年漢子知此人有來歷,急忙起身打躬,說道:“弟子甘拜老師父為師,請老師父受徒弟一拜。”
老僧合掌吟道:“本性好絲桐,塵機聞即空。一聲來耳裏,萬事離心中。清暢堪銷疾,恬和好養蒙。尤宜聽三樂,安慰白頭翁。”
青年漢子跪伏于地,說道:“弟子袁炳輝,任英屯多年為農,俠義遠近聞之;自小喜歡舞槍弄棒,擲石鎖,踢木樁;可是要得到真功夫,只憑一般的武師指點不行。弟子觀老師父佛風道骨,內力非凡,真是鐵鞋踏破無覓處……”
老僧閉目不語。
袁炳輝道:“師父是不是覺得我的根基不行?”他抄起一根木棒,施展全部本領,騰挪閃躍,進退便捷,一根棒舞的呼呼生風。引得河裏戲水的那個無賴和衆小孩也跑來觀看。袁炳輝舞的興起,棒如旋風,只見其人,不見其形。無賴驚得張大了嘴巴,衆小孩也拍手喝采。袁炳輝大汗淋漓,氣喘籲籲,再看老僧,已端坐毛驢,鼾聲大作。
袁炳輝面有愠色,說道:“師父,您是不是覺得我的技藝不精?”
老僧睜開眼睛,說道:“你的棒圓而不方,滑滌而無弧棱,你向我打。”
袁炳輝将棒向老僧打去,老僧一揮袖子,那木棒仿佛被吸住一樣,粘住老僧的袖子,袖子向東,木棒向東;袖子向西,木棒向西。袁炳輝拼命拽拉,也無濟于事。忽然,老僧的袖子向上一揮,那木棒嗖的向半空飛去,折為兩截,散落于地。袁炳輝倒退數步,趔趄着跌在地上。
老僧笑道:“棒子是圓的,而要當方的用,表面雖光滑,而要當成有棱角,絕非易事;老納我十年鍛煉臂力,六十年養氣,才練到這個地步,不受苦中苦,難為人上人啊!”
老僧說完,一拂袖,毛驢得得得地跑遠了,消失在迷蒙的土路上……
袁炳輝怔怔地坐在地上。
無賴和孩子們發出轟然大笑。
在這笑聲中,還有一種銀鈴般的笑聲,似乎從遠處飄來……
袁炳輝循聲望去,只見土路上揚起一團煙霧,一個年輕嬌媚的小女子推着一輛獨輪車悠悠而來;這小女子生得亭亭玉立,水靈靈的就像剛從河裏撈出來的嫩藕兒,白得像涼粉兒;身穿碎花白夏布衫,白夏布長褲,踏着清脆的步子。車上坐着一個鮮花般的妙人,氣度幽雅,神韻驚人;她身裹一團白紗,如一團白雲,仿佛置身雲端,輕飄飄的。又像從那裏飄來的一股香風,将一支淡雅、鮮麗的白蓮花被風搖曳着飄過來;一張小白菩薩臉嵌着一對黑亮的水銀,露出令人銷魂的微笑。
袁炳輝及衆人都看呆了,茫茫原野還沒有見過這神奇美麗的女子。
無賴揉了揉眼睛,涎水淌了下來。
一個大一點的孩子推着無賴說:你有膽兒握一握那仙女的三寸金蓮麽?
無賴瞪大了眼睛,一瞥嘴,嘟囔着說:有什麽不敢的?天砸下來,碗大的疤!我就不信閻王爺給她們開那麽大的門縫兒!
獨輪車嘎吱嘎吱地開了過來。車上那女人伸了伸腰肢,花朵般的身子飄了飄,恰好露出一只紅酥稣的三寸金蓮……
無賴如箭一般沖了上去……
袁炳輝想要阻攔已來不及……
那無賴手掌剛觸到女子腳趾,忽然打了個寒噤,渾身僵直如冰,伸出的手再也縮不回去了。
兩個女郎盈盈一笑,飄然而去。
袁炳輝和孩子們圍住無賴,只見他兩眼直視,瞳孔散光,左臂耷拉,右臂僵硬,手掌向下,仿佛在取什麽東西。幾個小孩焦急地推他,他毫無知覺。
袁炳輝見勢不妙,慌忙去追那兩個女郎。
“兩位妹妹,快給他解了穴吧。”
推車的女郎頭也不回地說:“水音,不要理他。輕薄兒郎,真該千刀萬剮!”
袁炳輝氣喘籲籲地說:“他雖然無聊,但他上有老母啊!”
車上被喚做水音的少女緩緩回過頭來,看到袁炳輝着急的樣子,嫣然一笑,一揮纖纖玉手;那無賴長籲一聲,活轉過來。他伸開手掌,只見掌心有一個黑點,原來是少女鞋上的泥痕。
袁炳輝見無賴腳下有一個紙團,趕過去拾起來,展開一看,上面寫着一首小詩:
永是江湖客,天地亦茫茫。
清爽觀煙雨,濁塵落書香。
寺鐘日日響,閨燭年年長。
師從無由處,勸君莫彷徨。
袁炳輝再看那兩個女郎,已無蹤影……
袁炳輝雖然讀過幾年私塾,但是反複看這首詩,也是不解。疑疑惑惑,也無可奈何,于是将這首詩藏在懷裏。
又過了一個月。
春光融融的任英屯,光明和清鮮,一陣暖風吹來,濃郁的麥香漂浮着,莊稼人的鞋底像抹了油似的再也閑不住了。男人們整理着套繩,喂飽了馬;女人們收拾着簸萁、籃子,縫補着破了的口袋。
袁炳輝走在鄉間的小路上,草綠得像翡翠,點綴着星星點點的黃花;綠蔭匝地,呢喃的燕子穿蔭而過,遠遠的地平線上,蕩漾着透明的氣流,白汪汪的像滾滾流動的大水。灰色的、土色的山溝溝裏,不斷地傳出汨汨的流水聲音;那條間或一小群一小群牛羊的陡峭的山路,逶逶迤迤,高高低低。從路邊亂石壘中伸出一支盛開的野紅杏,惹得袁炳輝不忍再走。
他還是闊步向前走去,因為他要找到鎮上的私塾先生,破一破詩謎。
午後,袁炳輝才拐上大道;走了一程,忽然,遠處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,并卷起一片塵土。袁炳輝見路上有個有個老婦人蹒跚而行,一匹脫僵的騾子瘋狂而來……
情形危急。
“危險!”他大聲叫道。
袁炳輝沖了上去……
這時,半空中卷起一陣旋風,一個老僧沖上前,用單掌輕輕一推,那只受驚的騾子便撞向一邊;那只騾子毫不示弱,氣急敗壞的朝老僧撞來……
老僧坐在地上,騾子從他腹部踏過……
騾子遠去了……
袁炳輝擔心地朝老僧望去,只見他雙手合十,口念“阿彌佗佛”,微微一笑,拍打拍打塵土,揚長而去。
袁炳輝再一看那個老婦人,身輕如燕,轉眼即逝……
袁炳輝早已認出這位老僧就是那日見到的老僧,這位老婦人莫非就是那位姝女?他真的很疑惑……
來到鎮上時,天已擦黑;暮色在背陰處濃了起來,到處是蒼茫煙流,只有東邊的高山頭上還留着一片夕陽;鎮上的房屋呈現出一片淺灰色,乳白色的炊煙和灰色的暮霭融合在一起,像是給牆頭、屋脊、樹頂、和街道都罩上了神秘的色彩,使他們變得若隐若現,飄飄蕩蕩。一群牧童趕着牛群從街市穿過,一個騎在牛背上的小牧童吹着短笛,笛聲凄涼、委婉……
袁炳輝走進私塾,先生還沒有回家;他把那個詩條遞給先生,先生看了看,說道:“這是一首隔句詩頭詩,有寓意啊!”
“什麽寓意?”袁炳輝迫不急待地問。
“小夥子,你是練武的吧?”先生問。
袁炳輝點點頭。先生撚着山羊胡說道:“這首詩暗示你到武清縣永清寺拜師。”
“寺裏一定有高人。”
“寺裏的住持海丘法師是一位高僧,他祖籍湖南,曾經東渡日本弘法,深谙奇功,極有內力,禪術遠近有名,人稱‘鐵肚子和尚’。”
袁炳輝拜師心切,在鎮上匆匆吃了點包子,立即趕往武清縣永清寺。
第三天傍晚,袁炳輝找到了永清寺。寺院掩映在一片蒼翠的樹林中,山門朝西,門上挂着一塊金色匾額,上書“永清寺”三個大字。稀松的樹林中,漏出些倦了的鳥聲來;旁邊有一條小溪,在夕陽中像一條銀帶閃爍;小溪汨汨而流,進入山門旁邊的蒼龍浮雕之中;那蒼龍吐出溪水,使之落在下面的一只石雕蛤麽嘴中,淙淙有聲。袁炳輝見這寺院紅牆綠瓦,整潔清幽,寺門緊閉,于是上前叩門。一忽兒,一個小僧露出個腦袋,問道:“先生有何貴幹?”
“我要見法師。”
“你找我師父有什麽事?”小僧的眼睛熠熠發光。
“我有急事,你快去通報。”
“你叫什麽名字?”
“我叫袁炳輝,滄州任英屯人。”
小僧一聽,頭搖得似波浪鼓兒。“師父有交代,不見!”寺門砰的關上了。
袁炳輝急得使勁敲門,毫無動靜。
半空中傳來一陣女子銀鈴般的笑聲……
這時,天色已黑,皎皎月下,一座座屋頂上的琉璃瓦閃着陰冷的光。袁炳輝隔着門縫一瞧,裏面塔影沖霄,松聲滿耳;一株古松下,放着一張桌子,一條板凳;桌上晾着幾碗茶,一個錢筐籮。樹上挂着一口鐘,一個老僧坐着打盹兒。
袁炳輝心中一橫,索性跪在地上,朝寺門作揖。
這時,樹林裏又傳出一陣嘻嘻的笑聲。
他四下望去,毫無人跡,只有涓涓的水聲。
夜來了,寒氣襲人,月光給寺院塗上了一層奶油般的黃色,一朵蓬蓬松松的雲彩,在天間浮動,徐徐飄去;夜風卷帶着野花的清香、濃重的泥土香、樹葉的潮氣,紛紛襲來。偶而飛過的山鹬苦悶的呼叫聲,劃破了這夜的寂靜。
袁炳輝又冷又餓,于是站了起來,走到寺院後面。他想探個究竟,攀上牆去。
他驚呆了:這是寺院後面一個獨特的院落,牆頭上鑲嵌着一個個耀眼的紅燈,燈內燃燒着閃爍不定的燭火。
紅色,是激動人心的顏色,是陽光的顏色,是鮮血的顏色。
院裏幾張席子上晾着椰棗,支架上挂着洋蔥、辣椒,順牆放着一袋袋小麥、蠶豆,有的縫了口,有的還敞開着。向北是三間朝南的精舍,一轉既是回廊,用帶皮杉木做的闌柱。西面有一片花圃,白盈盈的扶桑,黃橙橙的迎春花,粉微微的桃花,紅豔豔的杏花……争奇鬥勝,異常幽秀。
袁炳輝躍了進去,沿着牆根,來到西邊的窗前,隔着藕荷色的窗簾向屋內望去:一盞清油燈放在臨窗的烏木書桌上,左邊案頭堆了一疊書,有《論語》、《武經》等書。中間放着花瓶、筆筒、硯臺、水盂。一張架子床放在靠裏的右邊角落,床上吊着輕紗帳幔;暖紅秀被,晴翠床單。鬥大的一個汝窖花囊,插着滿滿的一囊水晶球白菊。壁上挂着一柄紫檀寶劍,還有一幅《俠女盜仙草》的古畫。
袁炳輝又來到正廳窗前,正中紫檀木案上,供着一盞紅燈,紅的耀眼;兩側擺着紫檀木的高矮幾,矮幾上的素花瓶裏插着一大束白盈盈的桃花;正壁懸了一軸小中堂,畫着義和團廊坊激戰的工筆彩畫,兩側有一幅對聯,左聯是:乾坤有正氣;右聯是:廊房随煙雲。東壁下面是藤椅,西壁有一排兵器架,有刀槍劍戟等兵器。
袁炳輝又來到東廂房窗前,透過淡紫色窗簾往裏望去,北牆下也有一個木架床,輕紗幔帳;旁邊有一個紫檀木雕花文玩架,上面擺着銅的瓷的工藝品,最惹人眼的是一匹泥燒的赭黃色的戰馬,昂首翹尾飛奔,神色非常生動。壁上懸着寶劍、木琴、花瓶。屋內有個屏風,圖案是一朵朵紅豔豔的牡丹;屏風後有個雕縷精致的木浴盆。
袁炳輝思忖:這裏一定是小姐的閨房。
這時,從前院傳來一陣女子爽朗的笑聲。
袁炳輝連忙躲到旁邊一顆古松樹後。
兩個風姿綽約的少女提着燈籠走進院內。袁炳輝一看,正是那日見到的那兩個神奇女子。
“那個呆子還跪在那兒,真有意思!”一個少女說。
“不受苦中苦,難為人上人啊,嘻嘻!”另一個少女笑道。
“水音妹妹,你給他送點蘋果去,他可能餓壞了?”
“嗬,水印姐姐,你還心疼他了,有意思了吧?”
“去你的,傻妹妹,我在為師父物色高徒,你開我的玩笑,瞧我不撕碎你的嘴!”
兩個少女嘻笑着扭打着走進西廂房。
袁炳輝聽了她們的一番言語,心中暗喜;于是走進窗前。
水音和水印并排坐在床上,水印穿一件玉色紅青鴕絨三色緞子拼的水田小夾襖,束着一條柳綠汗巾;水音身段靈巧,像一只鼬鼠,穿着一件白色狐皮鬥篷。
水音撅着小嘴道:“現在就像個隐士,都快悶死了!”
水印道:“竹籬下,忽聞犬吠雞鳴,恍似雲中世界;芸窗中雅聽蟬鳴鴉噪,方知靜裏乾坤。不須隐遁深山,只消居于寺院田園,遠離喧嚣紅塵,有如居于雲中仙境。”
水音道:“姐姐,你難道就忘了死去的幾十萬義和團、紅燈照的兄弟姐妹了麽?是慈禧那老賊出賣了我們;洋鬼子打進北京城,慈禧西逃,後來和洋人簽訂了《辛醜條約》,賠了那麽多銀兩,我真恨不得殺了慈禧那老賊!”
水印嘆了一口氣,“師父的血海深仇比你要深啊!他一家老小被清兵殺了七口,被迫逃遁日本……”
水音噓了一聲,說道:“小心隔牆有耳。”
水印走出屋門,袁炳輝急忙又躲到樹後。水印四下望望,返回屋內。
袁炳輝等了一會兒,又來到窗前。
水印正在案上揮墨,水音在一旁觀看。
水印寫的是宋代詩人陸游的《客去》詩:“相對蒲團睡味長,主人與客兩相忘。須臾客去主人覺,一半西窗無夕陽。”
水印的書法秀逸潇灑,甚有男人氣。
水印嘆道:“陸老夫子在功夫修煉方面,已經達到很高的境界。他說練功要肌體放松,心神入虛,進入忘卻自我,意不沾身,似睡非睡的心境安定狀态。這首詩的一、二兩句,正是寫了詩人已進入這種練功狀态,他坐在蒲團上,雙目閉合,神情安祥,無私無念,似醒非醒,達到了深度入境。三、四兩句,強調詩人入境時間長,意守十分專一,共同打坐的客人已經離去,他毫無知覺,太陽已經西沉,他也沒有察覺。只有功夫高深的人,才能做到這一點。”
水音道:“師父也常告誡我們,哀哉衆生,常為五欲所惱。”
水印緩緩道:“五欲惑亂本心,而練功者唯有踏破這五道門坎,才能做到無累無所欲,這是功夫的最高境界,可是不知這個袁先生是何種人士?”
水音道:“不知他有沒有這個造化?”
水印打了個哈欠,說道:“妹妹,我困倦了,先去洗浴,你先練書法;然後我再叫你洗浴。”
水音點點頭,水印出屋去了。
水音換了一張宣紙,鋪開顏料,精心地畫起來。